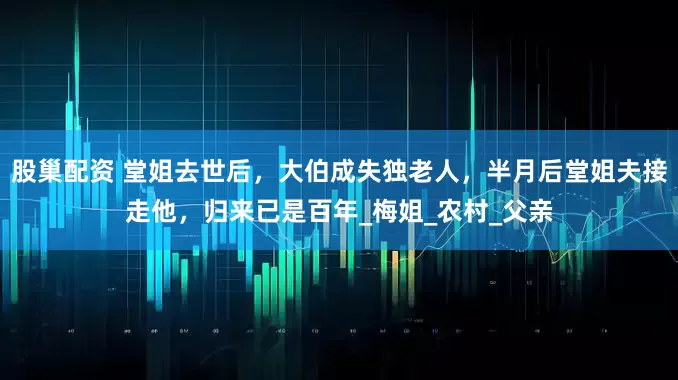
接到母亲电话那天股巢配资,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,我看了眼来电显示,心里咯噔一下——母亲很少在我上班时间打电话。
“小娥啊,你大伯回来了,人已经不行了,你赶紧回来见最后一面吧。”母亲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带着一种我熟悉的、农村人面对死亡时的平静与哀伤。
我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,五月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大伯要走了?那个沉默寡言的大伯,终于要卸下肩上的担子了?
挂断电话,我请了假,和丈夫一起开车回了村里。车窗外股巢配资的景色飞速后退,我的思绪却不断往前,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陕南农村。
父亲那辈兄弟三人,大伯陈大山是长子,二姑排中间,我爹是老幺。爷爷是从四川逃难过来的,在我爹十岁那年就去世了,留下奶奶和三个孩子。大伯作为长子,十五岁就扛起了养家的重担。
“你大伯啊,老实得像头牛。”父亲常这样评价他的大哥,“小时候分吃的,他永远拿最小的那块;干活,他永远挑最重的担子。”
展开剩余84%八十年代家里穷,大伯结婚晚。大娘是隔壁村子的,天生腿脚有疾。
别看大娘腿脚不便,但人勤快,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大伯回家,总有热饭等着他。日子也是越来越有盼头。
可惜好景不长,大娘进门的第三年怀孕了。那时候农村生孩子都是请的接生婆,自己在家生。
大娘生产时,堂姐的一只脚先出来了,眼看大人孩子憋的不行,接生婆不得已做了侧切,才把堂姐接生出来。大娘月子里落了病,几个月后就撒手人寰。
大伯从此既当爹又当娘。那时农村还没大型机械,栽种收割全靠人力。村里人都记得,农忙时大伯背着堂姐下地,用布条把孩子绑在背上,弯腰插秧时,堂姐的小脑袋就跟着一点一点的,像只打瞌睡的小鸡崽。
“那时候你大伯整个人都垮了,”父亲曾经告诉我,“但他一滴眼泪都没掉,只是更沉默了。”
堂姐小梅比我大五岁,是我童年最亲密的玩伴。大伯去煤矿挖煤时,小梅姐就寄养在我们家。我至今还记得她背着我满村跑的样子,两条小辫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“小娥,你要好好读书,”小梅姐总是这样对我说,“只有读书才能走出这大山。”
她做到了。小梅姐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,毕业后在西安一家大公司工作,每月工资比我们村一年收入还多。她把大伯接去城里,再也不让他下井挖煤了。
后来小梅姐认识了堂姐夫张建军。堂姐夫是城里人股巢配资,父母都是普通工人。大伯怕小梅姐嫁过去受委屈,拿出全部积蓄给她买了套小房子。那笔钱是他用命换来的——在漆黑的矿井下,一铲一铲挖出来的血汗钱。
车子一个颠簸,将我从回忆中惊醒。窗外已经能看到熟悉的村庄轮廓,我的心却越来越沉。
回到家时,院子里已经聚了不少人。农村就是这样,谁家有个大事小事,邻居们都会自发来帮忙。我挤过人群,走进里屋,看到大伯静静地躺在炕上,脸色蜡黄,呼吸微弱。
“小娥来了。”父亲轻声说,拉着我走到炕边。
我握住大伯的手,那手上有厚厚的茧子,是多年劳作的痕迹。令我惊讶的是,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,衣服也干净整洁,显然这些年被照顾得很好。
“姐夫呢?”我问。
“去镇上给你大伯灌氧气,你大伯这会全靠氧气吊着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“这孩子,十五年如一日地照顾你大伯,比亲儿子还亲。”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十五年前,小梅姐怀二胎时意外摔倒,大出血没救回来。那场葬礼上,大伯一言不发,却在葬礼结束后病倒了。半个月后,姐夫上门把大伯接走,说:“爸,小梅不在了,我就是您儿子。让我替小梅和妞妞给您养老送终吧。”
当时村里人都说,姐夫这是客套话,过不了两年就会把老人送回来。可谁也没想到,这一接就是十五年。
“爸,我回来了。”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转头看去,姐夫风尘仆仆地站在那儿,手里提着氧气袋。他比上次见面老了许多,两鬓已经斑白,但眼神依然温和坚定。
他快步走到床边,熟练地检查大伯的情况,然后轻声说:“爸,小娥来看您了,您睁眼看看。”
大伯微微睁开眼睛,浑浊的目光在姐夫脸上停留片刻,嘴角扯出一个几不可见的微笑。这个笑容让我心头一颤——在我记忆中,大伯很少笑。
那天晚上,我们轮流守在大伯身边。夜深人静时,姐夫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,握着大伯的手,轻声说着什么。我端了杯热水进去,听见他在说:“爸,妞妞下个月就高考了,她说要考医学院,将来当医生救人。您一定要坚持住,等着看她拿录取通知书啊……”
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妞妞是小梅姐的女儿,三岁就没了妈妈,是大伯和姐夫一起把她拉扯大的。
第二天清晨,大伯的情况突然恶化。姐夫跪在炕边,声音哽咽:“爸,您别走……再等等妞妞,她马上就回来了……”
大伯的呼吸越来越弱,最后看了姐夫一眼,缓缓闭上了眼睛。他的表情很安详,像是终于卸下了所有的重担。
姐夫伏在大伯身上,肩膀剧烈抖动,却压抑着不哭出声来。这个照顾岳父十五年的男人,此刻像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一样无助。
葬礼那天,村里来了很多人,姐夫穿着孝服,跪在灵前,一遍遍给来吊唁的乡亲们磕头。他的眼睛红肿,声音沙哑,却依然周到地安排着一切。
“建军这孩子真是难得,”村里的老人感叹,“十五年啊,就是亲儿子也未必能做到这样。”
“可不是,”我母亲抹着眼泪说,“大山哥这十几年在城里,吃穿用度都比在村里好。建军每月都带他去医院检查,天冷了还给买羽绒服……”
大伯终于躺在了大娘和小梅姐旁边,也算是一家三口团聚了。
葬礼结束后,姐夫一个人坐在大伯的坟前,久久不愿离去。我走过去,递给他一瓶水。
“小娥,”他声音沙哑,“你知道吗,爸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妞妞。他说……说让我一定要看着妞妞上大学,结婚生子……”
我点点头,眼泪又涌了出来。姐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老旧的钱包,小心翼翼地打开。里面有一张大伯、小梅姐和他三人的合影,照片已经泛黄。
“这是我和小梅结婚那年拍的,”他轻声说,“爸一直带在身上。小梅走后,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和妞妞……”
回城的路上,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,思绪万千。大伯的一生是不幸的——幼年丧父,青年丧妻,晚年丧女。但他又是幸福的,因为他有一个比亲儿子还亲的女婿。
姐夫用十五年的实际行动证明,亲情不只是血缘,更是责任与爱的延续。他本可以在小梅姐去世后开始新生活,但他选择了承担起照顾岳父的责任。而大伯,也用他沉默的爱回报了这个女婿。
善良终将得到善良的回报。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,姐夫和大伯的亲情让我相信,真情永远存在,只是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。
车子驶入城区,我的手机震动起来。是姐夫发来的消息:“小娥,爸的遗物我整理好了,有些东西想交给你保管。周末有空来家里吃饭吧,妞妞也想见见你这个姑姑。”
我擦掉眼泪,回复道:“好,我一定去。”
窗外,夕阳将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,就像大伯生命中最后的那些年——虽然短暂,却充满了爱与温暖。
发布于:河南省顺阳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